

君思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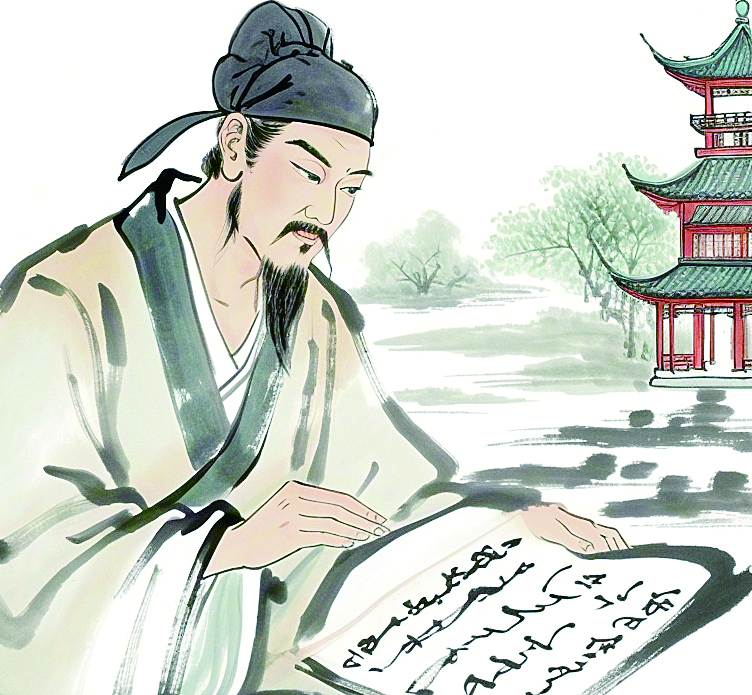
□ 杜锦涛
临安城内的秋风总是清凉,里面混杂着江南独有的气息。各处酒楼茶馆顺着街道铺开,连绵不绝。勾栏里说书人的一声惊堂木,也不知惊起了多少梦中看客,声音回响在西湖不远处的凉亭里,吹凉了文人士子的杯中淡茶,也带走了这个繁都的热闹。
李思南老想着自己还在临安的院子里,手里捧着一本书,听那回响在深街柳巷处的阵阵秋风,周围的铁马戈矛之声便也闻若不见。
西湖是临安城外的一处佳境,也是当世诸多文人墨客吟咏游玩之处。李思南不像他们一样寄情山水,只是在父亲的陪伴下去过几次,记得当时旁边的茶楼里传出说书先生讲的岳飞的故事,心里好奇时却又听见有人吟诵“满江红”,心里默记。此时西湖的清波荡漾,惊起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鸥鸟,纷纷飞向湖中小亭。
“当年汴京的勾栏里,也是有杨六郎的故事的。”父亲的回忆让他忘了看西湖边上的卖糖小贩,也渐渐地让他记起了当时的自己并不叫李思南。
过往的行人们带着微笑,正说着哪里哪里的姑娘曲唱得好,引得军将忘了练兵,也来捧场,李思南也忘记了西湖边上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,就只剩下了他与孤零零的西湖,没有风的西湖。
江湖上的说书人最有故事,一身风尘,出落于勾栏酒楼之间,凭一张利嘴来取得钱利。他们口书成诵的故事流传于大街小巷,使得妇孺皆知,他们沉醉于这种口说得利的营生,但不曾想起故事中的世态炎凉,人间百味,只不过是人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,也没有人真正放在心上。
李思南记得父亲说,汴京的说书人说过当年的杨门忠烈,说过岳飞大破金兀术,说过魂断风波亭。听客们只听说书人的,只看汴京的,临安的,却不向外走,也不向外看,以至于为何由汴京到了临安,他们都没放在心上。
他们很清闲,很平静。正如西湖边上的秋风一样。
秋天的雨是凄凉的,闺阁女子念叨两句“凄凄惨惨凄凄”,便去吆喝着侍女把琵琶送来。临安城最热闹的皇宫两侧今日没了吆喝的小贩,他们都怕雨,连宫里人也怕。
畏畏缩缩的,不敢出来。
天公自是清明,一繁一市,一华一都,一草一秋,也便是一安一京。
李思南感到天空下起了小雨,粘在头上微湿,刚才在想着自己以往的名字,但有时却忘记背《满江红》。自是两难间,有时的他也会忘了头上的秋雨正盛,他倒想哼出几句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但却是顾及不思,也忘了。
但也是,有的人忘记了以往的名字,只记得现在的名字,李思南想起了临安的自家院子,想起了临安城内的浮华云烟,却总是繁华胜了悲戚,如当年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不过那画的,却是汴京。
耳边又传来了一声惊堂木,李思南习惯性地抬头,便看见一群听客围在说书先生周围。他恍惚间看到岳飞魂断风波亭时说书先生竟有泪落下,心想那说书先生也是个有情义的人,也想着,他是不是能将《满江红》出口成诵。
李思南听着,便苦笑一声,原来这历史的结局如此相似。
就像这秋雨,下是必然下的,汴京和临安肯定都下秋雨,不过肯定不同。
李思南突然想去看看西湖,便不再想临安城里自己的院子,也不再想自己已经逝去的另一个名字,因为秋雨已停了。
李思南这才想到,自己不在临安。
雨停之后的初阳斜照,却是那般的刺眼,而李思南,却听见了他不想听到的声音——金戈之声。
为什么不在临安呢?为什么自己又不执着于寻找自己的名字?而为什么自己将那忘却的《满江红》背得滚瓜烂熟呢?
像是岳飞梦中的北宋回不来了,李思南的临安也回不来了,他的南宋也回不来了。
蒙军南下,大破山河。
于是百姓不再去临安,说书人的弄堂也空无一人,那一纸笑谈也将灰飞烟灭。
只是,李思南这个时候,很想去西湖,他仿佛又想起了不知去往何处的父亲,也终于在下一次秋雨再来临前忆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南宋临安,君时未忘,见而思之,其名为北,意指中原山河。
只是南宋亡了,吾又思南。
君名思南,字安之。

